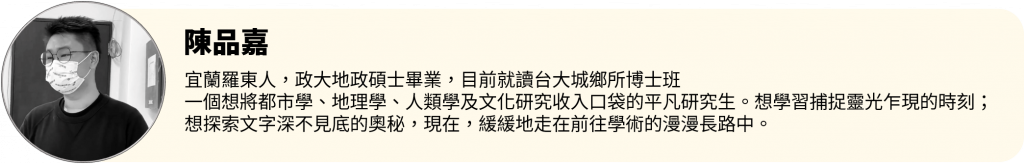撰稿者:陳品嘉
審稿者:郭泓毅
順著第一場講座的脈絡,我們知曉在面對疫情干擾的情況下,田野工作該如何進行。與過往實體現地的田野空間相比,透過更多的科技設備,協助研究者完成田野研究,讓田野不再侷限於一種樣貌,回應了該週的主題,即「田野在哪裡?」,無處不是田野成為了不確定時代中的研究態度。
第二場的講座延續虛擬田野的議題,並進一步聚焦於教育場域中,田野這項專業技能,老師們該如何教導,學生們又該如何學習?在不確定的時代中,場域的限制、科技教具的使用,遠距離建立關係,多元的方法學等皆是傳統田野課程中鮮少探討的新議題。本次講座邀請到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的鄭肇祺老師,以及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黃舒楣老師,共同借用來自原鄉部落的紅藜,作為這次講座主題的楔子,開展出有關自我與田野之間的關係與理解方式,並從個人近年的研究脈絡,同時試圖回應目前在疫情之下田野進程的困境,導引出田野該如何教、怎麼學。

鄭肇祺:「我是一位吃喝玩樂的人類學家」
對一般大眾而言,人類學好像是一個難以捉模的學科,時常與叢林、泥土、土著等對象牽扯在一起。事實上,人類學可以很接地氣,可以從人類與土地的互動,以及因土地而生的產業著手,探查並剖析人類社會的樣貌。來自臺東大學的肇祺老師對於田野調查的價值觀,即是以此脈絡為出發,藉由農業、漁業等貼近土地的初級產業,衍伸諸多的研究課題。這些產業背後都富有濃厚的「人味」,對此提供了肇祺老師在研究的旅途上獲得源源不絕的靈感。
研究的主軸確定了,但要如何進入田野呢?肇祺老師指出,首先當然是要和地方建立關係,這是田野行動最重要的一步,也是未來發展成田野教學時,理應進行的前置作業。換言之,在建立關係的行動中學習,是田野教與學的拓展關鍵。在進入田野之前產生的焦慮和不安該如何應對呢?肇祺老師說:「我對於進入田野這件事情基本上不會感到緊張,因為可以在裡面享受吃喝玩樂的樂趣,我把自己稱為『吃喝玩樂的人類學家』。」這是肇祺老師本人對於田野研究的註腳,也就是說,他將田野過程看作是一場美好的旅行,享受過程中的不期而遇,加上鄉野美食和山林美景的相伴,自然而然就化解了內心的焦躁感。肇祺老師也因此鼓勵研究者,如果想不到研究的方向,與生活相近的飲食文化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題材。

前面提到有關肇祺老師的研究,農業、漁業是他主要探究的議題。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,肇祺老師接觸到紅藜這個作物。紅藜在肇祺老師前往臺東之前,就已經成為政府大力宣揚的部落作物,包括水保局、農改場、臺東縣政府等,皆將紅藜與原鄉部落綁在一塊。肇祺老師在研究的過程中,認識了當地部落的返鄉青年─「紅藜先生」。起初紅藜先生透過環島旅行,帶著裝滿部落物件的推車,沿途替部落募款,為了有更好的醫療資源,他選擇從經濟問題著手,之後便留在部落種植紅藜,嘗試藉由紅藜產業改善部落的經濟困境。然而紅藜在過去是只是配角,大多都種在小米旁邊,用於驅趕鳥類用。當紅藜從配角躍昇為主角時,反倒會衍伸出一些問題,例如要讓部落將紅藜作為耕種的主要作物時,如何說服當地的農夫,如何解釋紅藜的重要性等議題。紅藜先生的行動啟發肇祺老師意識到部落的經濟處境,也認知到產業之於部落的重要性。
而肇祺老師是如何與紅藜先生建立關係呢?除了邀請紅藜先生到自己課堂上講述紅藜從生產到銷售的網絡關係,包含鐵花村、部落族人與製作食品者之間的互動之外,肇祺老師也從消費者的角度親身購買紅藜產品。在傳統人類學中與資本掛鉤的行銷手段,都是會招致嚴厲的批判,但他卻認為,市場經濟仍是目前人類社會重要的一環,因為這是農、漁民的生產動機,應該要更深入地了解市場機制,才能知曉該如何運用市場創造更好的價值,也透過這些農、漁民的生命故事帶動臺東在傳統產業發展過程的省思。肇祺老師認為,由消費串起田野,可能會與過往看待人類學的視角不同,但這正是人類學的另一種嘗試,去解析不同的田野面貌。
肇祺老師認為,從紅藜這個作物可以衍生出許多議題值得探究。如紅藜成為青年返鄉的動機,也是因為紅藜的出現,使得部落的產業開始轉向,在物與人之間形成一個相互連結的網絡,構築肇祺老師對於田野研究在教與學之間的橋樑,並提供後續持續研究的能量。

黃舒楣:尋訪空間中的裂縫與細痕
「如果可以接受隨時可調整、可開放,接受自己研究關鍵字有驚喜出現的話,那也許田野調查就是適合你的研究方法。」對於各種未知與可能性抱持開放態度,可說是舒楣老師對於田野的核心價值觀。
田野在哪裡?是舒楣老師在研究生涯中不斷詢問自己的問題,而近幾年也因疫情的影響,讓她對於方法有了新的看法。她分享自己研究上海監獄的例子,因為疫情無法親赴現場勘查、看盡一切的情況下,科技輔助的訪談與檔案蒐集成為她完成田野的重要助力。
提到如何進入封閉或專門知識的場域,舒楣老師認為是需要長時間的經營,逐漸地鬆動阻隔場域的圍牆,同時也要認清現實,做好可能永遠無法進入的場域的心理準備。但同時可以保持著對於研究方法的彈性與開放心態,既然無法進入,那可以從較外圍的場域入門,滾動式調整研究問題,將有可能發掘到其他重要有趣的議題,這也是研究有趣的部分。以上海的監獄研究為例,舒楣老師說,不僅是因為疫情使他無法親自到上海,那座監獄是無法供外人進入的。當時她透過轉換分析對象,以監獄周遭的街區為論述核心,搭配與居住在上海附近的研究生保持資訊的流通,最終還是克服了原本無法解決的研究限制。

對於舒楣老師而言,田野研究最重要的是從「當地人的角度」去瞭解問題、與問題解決的方法。對於學者而言,不只是去蒐集資訊,建立與地方的互信也是很重要的環節,進入場域不一定會解決真正的問題,但若能夠與當地人建立信賴關係,當地人願意分享後,是能夠透過他們的視野捕捉問題的本質。老師也強調當代我們看田野,要以開放的態度來回應「誰研究誰?誰來提問?」的問題,進入場域時,自己不會是唯一的研究者,預設的報導人也可能同時進行著自己的研究,有別於傳統,研究方與被研究方傳遞訊息的角度將不再單向。
提到田野經驗,舒楣老師認為自己是一位容易緊張的人,踏入田野前都會失眠,但如果能夠忍受對於不確定性的焦慮,勇敢推開田野的大門,踏入場域之後往往會遇見更多意想不到的驚喜!走入場域中,研究者能從中獲得多少收穫,取決於「接受不確定場域能夠有多少展開」;田野能夠多豐富,端看自己給予田野多大的彈性。研究者與田野之間產生一個超展開的互動,不僅豐富了人生的經驗,也替不確定的時代找尋新的研究取徑。

田野怎麼教?又如何學呢?
回顧講座,兩位老師都分享了自己對於紅藜研究的經驗與感想,雖然研究脈絡與角度並不相同,但共同的是進入田野時必須與場域關係人建立信任感。同樣地,對於田野研究的熱情,肇祺老師對於踏入田野的期待,他享受場域的美食、新奇與關係人的互動,就如同舒楣老師進入田野觀察時所抱持的好奇心與開放態度,提點同學們在面臨各種田野現場帶來的不確定性,我們應該以正面積極地態度,去化解內心不安的感受,最終反饋到關於田野的學習層面,才能完整體現田野帶给研究者的內涵與價值。
總的來說,田野工作是一場即使做了萬全的準備,仍會有許多的不確定在過程中顯露,連結到田野的教與學,轉化成一種無法具象化的流程,這需要研究者本身順應當時的田野步伐,慢慢地打開田野研究的大門。